
文 | 秦柯
说时代翻篇了,每个人都不否认。但是,到底翻了什么篇?好像也没谁能一五一十的想清楚说清楚过。本来嘛,这是时代的整篇翻过,不是哪一行哪一段,也不是哪一页,就好像学家治史,无论编年体还是断代体,无论是通史还是纪传,总能碰到的那些历史性的折痕,无法平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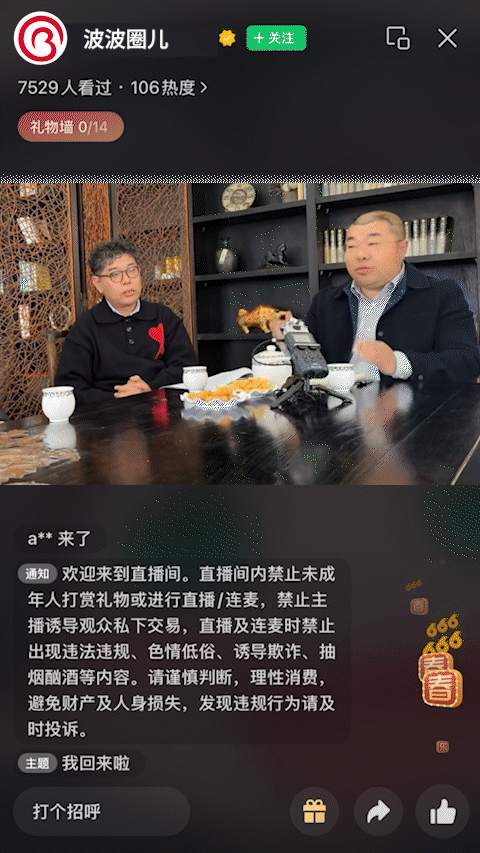
有句话叫“穿过现象看本质”,其实最难的不是“看本质”,而是“穿过现象”。
前几天拜访北方一位酒商,我说自己最大的焦虑是年轻人不喝白酒了。他笑着摇头,大手一挥,指了指身边85后的副总,“不对,他们喝!”
我又问:“你儿子喝吗?”,他瞬间沉默。
极有可能,85后的副总喝,是现象;85后的儿子不喝,是本质。
最近,酒商社群直播号“波波圈”连续几天在谈“香型”,从酱香大众化到清香、米香的市场前景,有酒商直截了当地在评论区留言:“我们对选择什么香型不感兴趣,我们想知道怎么解决库存问题。”
作为一个具体问题,这种意见不一定具备代表性,但有代表性的是,它意味着厂家——也包括媒体或专家——与酒商,尤其是那些沉伏于一线市场的卖酒人,在决策焦点上出现了偏离。
对于厂家来说,香型是现象,社会库存是本质。而对于酒商来说,库存就是现象,动销乏力是本质。再进一步,对于消费层来说,购买力降级是现象,新需求得不到满足是本质……
“穿过现象”之难,难在现象的复杂性,难在需要一层层抽丝剥茧才能抵达真正的“第一性”。而从人类两千多年的哲学实践来看,抵达第一性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对第一性永远保持怀疑。
手头有一份出自媒体,但未经全面确认的数据,显示2024年白酒销量排名前19位的大单品——其中200亿以上4个、100亿以上6个、50亿以上9个——合计已经占据了行业总量的半壁江山。看上去,我们大可由此得出结论:集中化,势不可逆。
然而,如果再多问一个问题呢——这究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,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?
换句话说,白酒行业究竟会继续集中化进程,还是到了重新打开的节点?如果集中,是像啤酒那样向领军企业集中,还是像饮料那样向产品集中,抑或像洋酒那样向渠道集中?如果打开,是以当年五粮液贴牌方式打开,还是以保乐力加供应链整合方式打开,抑或是以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方式打开等等。
任何一个答案,都可以转换成一个值得怀疑的新问题,随之而来的又是一群等候选择的新答案。我只能说,不管是企业还是酒商,唯一无需怀疑的就是你的怀疑,不要轻易选择答案,因为在你今天选择答案的时刻,未来胜负已定。
人们爱说“选择大于努力”,这是玄学,其实选择恰恰是最需要努力的事情,在此刻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,是你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。
前几天我曾用同样的句式表达过自己针对产能的具体观点。当时与一位工商联领导交流,他说产能是当下中国制造业的核心问题,“白酒行业大概也莫能例外”。我表示同意,但需要说明虽然它是核心问题,却不是问题的本质,我认为“产能是现象的总和”,白酒行业尤其如此。
三十年来,行业翻云覆雨之中,无论是“看得见的手”——如消费税和八项规定——还是“看不见的手”——如贴牌时代和酱香热潮——最先搅动的都是产能曲线,而一旦拐点降临,最后负担的依然是产能曲线。
如果以产能为“翻篇”的折痕,这一篇是从2017年开始翻动的。
白酒产能在2016年达到顶峰的近1400万千升之后,随后便开始下行。2024年应该是又创了新低,有数据是600多万千升,但据说更接近真实的是不到500万千升。本该再核实一下,但想起沈腾老师的话:“都摔成这样了,还计较那三米两米有意义吗?”
巧合的是,这一时间节点正好和“酱香热”的骤然起落吻合。穿过现象看本质,其实这也并非巧合,一边是白酒行业整体产能的收缩,而另一边,茅台引领酱酒价值大幅提升的同时,客观上也为其他产区、香型和企业保守了价格空间。所以我认为,八年来,从整体上看,白酒行业事实上是在经历一个控量保价的历史过程。
没错,属于名酒的控量保价是这些年热度日升的话题,但属于白酒行业的控量保价,却是将近十年的集体无意识行动。
正是因为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头部企业,才长期保持着某种“量价齐飞”的惯性认知。而事实上,量价齐飞这一战线是在不断向中心企业收缩的,随着五粮液新年前后以“控量保价”策略赢得一片掌声,随着茅台1935垂直降维冲击中产市场,相信到今年为止,在主业领域还敢于宣称量价双升的白酒厂家已经屈指可数。
而对于数以万计的中小型或边缘型企业而言,大概在几年以前开始,连控量保价的篇也已然翻过去了,量价双跌的状态在大白酒产业领域正不断蔓延。
产能是现象的总和,如果它是本质,那就意味着解决了产能平衡就解决了行业发展,但事实是这样吗?如果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还试图在旧地图里寻找新世界,任由核心消费者继续老去,年轻消费者继续流失,如果存量市场始终被新物种包围,增量市场始终无所作为……产能就会永远过剩,反之,就会生机勃勃。
产能是现象的总和,也是寻找第一性必须穿透的迷雾。
已有0条评论